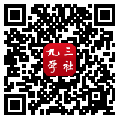俗话说得好:天下茶楼数中国,中国茶楼数四川,四川茶楼数成都。这话说得硬是好哇!说到成都茶楼呀,那确实是不仅有茶、有座、有趣,而且确实是川味、川风、川情甚浓呀!
说到成都茶楼的茶座趣,可谓在川籍著名作家沙汀的小说《在其香居茶楼里》反映得最为生动。
该文写到茶楼,是说成都人休闲聊天,洽谈生意,都要到茶楼去:成都人之间发生了吵架斗嘴等纠纷之事,往往也要到茶楼去讲理。
事实上也是这样,无论是建国前的20世纪 40年代,还是如今的新世纪新时代,我们都可在成都茶楼中看到这样的场面:有茶客一到茶楼,就扯开嗓子喊:拿碗茶来啰!于是茶倌就提着茶壶,摇摇晃晃、穿堂走过,边走还边兴高采烈地叫道:看座、看座、来啰、来啰!——走拢茶客身前,茶倌便把茶碗逐一摆放在茶客面前,然后架势一摆,径直把茶壶的长杆把伸过来,瞄准茶碗顺势一点,茶水便牵线似的溢满了茶碗。可谓点滴不漏,见好即收。
倘若此时茶客伸脖细瞧,茶倌还会幽上一默:嗨,让开点!不然把您的脑壳烫肿啦!
您看,这成都的茶座趣趣不趣?
而我呢,作为曾在成都生活多年的准成都人,每次回成都探亲,都要随号称老成都的么爸去茶楼坐坐,或闲聊闲摆,或铺棋对弈,或听听川戏、看看表演,这种边呷茶边休闲的心境,可谓胜过活神仙啰!
记得我第一次去成都茶楼,还是我已在川北广元市工作,回乡探望家人的时候。
回成都的第二天,父亲和么爸要我去一趟茶楼开开眼界。么爸也想趁机与我父亲在茶楼杀一盘。
虽然,么爸认为我这个晚辈与他们这两位老辈谈不上是棋逢对手,但到时也可作个替换输家的替手,因而么爸硬要我去。
我这是第一次到成都茶楼去散心,可谓是大开眼界了,既看到成都茶楼那种茶座趣的生动场面,还受到了茶饮文化的熏陶。
由于我的父亲是位从事茶叶生产、制作、研究达 30余年的高级农艺师,可谓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茶叶专家。他这次领我到青羊宫的一家较为僻静的茶楼。
到了茶楼,我们 3人刚刚落座,父亲朝我和么爸诡秘地一笑,然后扯起嗓门像模像样地吆喝了一声,随即有跑堂来到桌前。
父亲附着这位跑堂的耳边不知说了一些什么。
当这位跑堂笑着点头应声而去之后,父亲才释然地一展眉头,笑着对我和么爸说:今天让我给你们露两手吧!随着父亲一声吩咐,茶碗、茶盘、茶盖一一套摆在我们 3人桌前。
我给你们露一手!父亲边说边站起来,从随身携带的小提包里掏出一包云雾山绿茶。茶叶呈芽苞状,形如花蕊。父亲为我们面前的茶碗一一镊入一小撮,然后嘱跑堂将壶水冲入,并压上碗盖。顷刻揭盖,我即闻到了一股诱人的馥香。
此时,我们的茶碗中简直成了一个碧绿的海底世界:茶汤是海水,茶叶是海藻,间杂其间的茶叶芽宛如游累了的一尾尾小鱼儿,正在海藻丛中小憩。当我啜饮了几口,便想起品茶老手色、香、味俱臻上乘的话来。
美,太美了!我赞叹着。
注意,看我给你们露第二手!
当我正在品味茶中之味时,父亲又从他随身带来的小提包中掏出了一包云雾山银针茶。
父亲边打开袋封边给我们介绍:相传,700年前云雾山的银针茶是皇帝喝的贡品茶,种茶的是个多情的女神,她的名字叫淑氏,她为了追念亡夫,才种下这满山茶叶,留给了后代子孙。
这种茶乍看上去,一个个芽尖像银针,芽尖外面有一层层白白的茸毛,似抹了一层银,人们便把它命名为银针茶。
此茶加工质量要求高,产量却很低,整个占地面积万余亩的云雾山,每年只产七八百斤,其余大部分是次品毛尖茶。
这神奇的茶,这美妙的传说引起我极大的好奇,我迫不及待地希望饱饱眼福和口福。
父亲似乎看出我的迫切心情,不慌不忙地一边将茶叶逐一镊进我们的茶碗中,一边对我们介绍说,这种茶与众不同的是,冲泡时能两上三下,变幻无穷。
表演开始了。只见父亲从茶楼跑堂的手中接过刚烧沸的一壶热气腾腾的沸水,疾步冲到桌边,飞快地揭开茶碗上的盖子,熟练地把沸水冲满茶碗,再盖上碗盖。
这动作在几秒钟内一气呵成,过了约摸一分钟,父亲逐一打开碗盖,这时只见碗底的绿色茶叶如卧床军人突然听到命令,顿时全体起立一般,茶叶全数叶尖向上,迅猛射向水面,尖尖垂立,同时一团白气冲腾起来。
瞬间,碗中一部分茶叶开始下沉,形成狼牙式的对峙局面;然后,全部茶叶上下穿梭;最后,全部茶叶垂落碗底,真是其妙无穷。
我这第一次进成都茶楼,虽然最终因父亲的茶道即兴表演,而没有看到父亲与么爸难解难分的棋艺表演,但我却亲见亲尝亲闻我的父亲这位茶道专家借成都茶楼气氛而专为其亲人的演示及讲述,从而使我与成都茶楼就此结下了难解的情缘。
打这以后,我每次回成都探亲访友,都要挤时间与家人、亲友去坐坐成都茶楼,休闲品茗,玩味寄情,不亦乐乎!(翟峰 载于《人民代表报》2016年06月16日文学副刊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