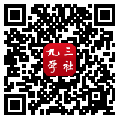“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岁尾年初,《中国诗词大会》火了电视荧屏,热了古典诗词。十六岁女孩武亦姝脱口而出的诗句出自《诗经•豳风•七月》,描绘的是西周初期的农耕生活图景。
文学之河源远流长。划着小船溯流而上,你会惊喜地看到,它是一条金光闪耀的河。
那闪闪发光的,就是诗歌。
劳作的男人和采芣苢的妇女走到河边来了,哼着小调在河中濯足。晨雾迷蒙,你看不清他们的面目。待移船近岸,人已散去,河边留下一片素朴简美的砂金石。数一数,305块。有人把它们排成了三个方阵,旁刻二字,“诗经”。
峨冠博带身佩长剑的屈原在河边徘徊,他手里捧着一块色彩奇绚的金石。那是诗人忧郁的心血与砂金淘炼而成,后人称之为“楚辞”。
汉魏晋长长的一段河岸上,来来去去诸多豪杰侠客隐士。仔细分辨,有曹操曹植阮籍嵇康陶渊明鲍照的身影,他们长吟短啸,手执光华灼灼;更多葛衣庶民吟唱着民歌野谣,从河中淘出金砂,被收贮到一个唤作“乐府”的房子里。
至唐朝,哎呀不得了,你的眼睛根本顾不过来:俊逸王勃、潇洒李白、沉郁杜甫,张若虚王维孟浩然王昌龄崔颢高适岑参白居易柳宗元李商隐,挡不住的八斗才情,压不住的泉涌灵感。诗人们行走于河岸河滩,吟诵唱和。这是碎金只能用来铺地面的时代,壮观辉煌至极:滕王阁盖起来了,太行山垒起来了,锦官城筑起来了……明月照春江,诗潮滔滔向东去。
月迷津渡,河流转了一个弯。柳永欧阳修苏轼秦观李清照辛弃疾陆游,宋代的诗人词人另辟蹊径,淘炼美丽的彩金。偶而豪放长婉约,举首高歌大江东去金戈如虎,浅斟低唱烟柳画船聚散离愁。
光阴梦蝶,功名是空,白朴关汉卿马致远张养浩袁枚,洒脱自适闲信步。元明清,散曲气韵生动,民歌余音绕梁,金滩上光烁点点。
“溪又斜,山又遮,人去也”。回首间,你看到的河流又是另一番景象。
世易时移,自“五四”以降,白话文和新体诗以更自由的表达形式成为文学主流,孰优孰劣的讨论几乎没有意义。世间万物,消长有时,古典诗词的衰弱乃必然。你也许要问:这来自远古的深厚源流,能否浇灌今日文化之树的根基?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真善美是人类永恒的追求。行舟生命之河的你我,何妨从古典诗词之河掬一捧清亮水,淘一把岁月沙,让人生旅程因欣赏美、感受美多几分欢喜?
美在韵律文采。韵文起于散文之先,是世界文学演化的通例。得益于汉文方块字的机巧和语音的四声变化,中国诗词读之琅琅,书之简约,形式美近于极致。从“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到“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从“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到“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起源于民歌的诗词,采用重复、押韵、对仗等形式,韵律巧妙回旋,节奏感和音乐性极强。诗歌用字千锤百炼,极尽文字之美,凝炼的诗句一旦译成外文,美感顿失大半,诚如木心先生所言“真能体会中国诗的好,只有中国人”。
美在山水自然。山水入诗,古已有之。南朝,谢灵运蹬着“谢公屐”,“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将山水由背景推到了前台,从此山水诗歌一发不可收。大漠孤烟,长河落日;云蒸梦泽,波撼古城;瀚海阑干百丈冰,西塞山前桃花水,太白鸟道峨眉巅,斜月沉沉海雾生……自塞北至江南,从高山到大海,无景不入诗,无诗不画境。“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诗歌关乎自然,关乎山水,关乎生活在山水自然中的人。山有山魂,水有水魄。河山之上,诗亦有魂。
美在人生情怀。“江月年年望相似,人生代代无穷已”,宇宙永恒,人生无常。诗歌里有执手偕老的坚贞,有路漫漫其修远的求索,有拔剑四顾的茫然叹息,有多病登台的独自沉吟。叹衣食之忧,“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悲家国难再,“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感悲欢离合,“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人生逝去的一切,留在了永恒的诗情里。
时光之河流淌不息。面对今日物质空前丰富,精神相对浮躁,俗气戾气渐重的社会,也许你又要问了:美又有什么用呢?其实,正如蔡元培先生所主张的“以美育代宗教”,小武亦姝已经给予我们启发了:看似无用的“美”之文化积淀,也许能帮我们,以及我们的孩子,更优雅地遣词造句,更热切地亲近自然,更善意地对待社会,更沉静地面对人生。
“天下之至柔,驰聘天下之至坚”,愿我们从美的欣赏和创造出发,少几分空虚庸碌的迷茫,多几分智慧豁达的定力,寻找到灵魂的归宿。(温志琳)